http://www.shm.com.cn/yantai/2004-05/03/content_1974.htm
I. 導論
一﹑開出說及對其批評
第二代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徐復觀先生﹑張君勵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在他們合著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中所提出:「……中國今雖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國之事業,然我們卻不能說中國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更不能說中國文化中,無民主思想的種子。」[1]因為,第一,「中國過去政治,雖是君主制度,但此與一般西方君主制度,自來即不完全相同。此種不同,自中國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說,即以民意代表天意。」[2]第二,「儒家復推尊堯舜之禪讓,及湯武之革命,則是確定的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並認為政治思想之理想,乃在於實現人民之好惡。」[3]第三,「……然本於人之道德主体對其自身之主宰性,則必要求使其自身之活動之表現於政治之上者,其進其退,皆同為可能。此中即有中國文化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簡單言之,就是君主制度並不是中國文化,尤指儒家政治思想,所必然推論的結果。不但如此,儒家的著重道德主体的思想實與君主制度成一矛盾。此一矛盾的解決方法,只有肯定皆平等為政治的主体之民主憲政,而民主憲政,亦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自身發展之所要求而成為可能[4]。
這種思想的進路,就成為日後所謂的「民主開出說」。就「民主開出說」的理論本身及其實踐問題,曾有一段很長時間的爭論。尤其是在五十年代,當代新儒家就這個思想進路曾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之間曾展開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政治的論戰。[5]而近年來,仍有不斷的討論在進行中[6],而其中一個比較尖刻的評論,就在語理分析上作出的質問。其大意是如此的:「如果『開出』的意思只是『不矛盾』 (意指邏輯上)的話,『開出說』其實沒有多大意思,因為所有文化都不與民主與科學矛盾,都能『開出』民主與科學。」縱使這個批評是正確的,我們仍有最少有兩個進路可以作出回應。第一,就歷史的意義而言,五四運動以來,新儒家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環境下需要靈根自植[7],要對於反對傳統的非理性思潮作出回應[8]。其理由為文化是一過去﹑現在與將來的連續体[9],故此,儒家是否與民主及科學矛盾這一課題實有其歷史意義。其實,除了歷史意義,儒家是否與民主及科學矛盾還有一理論上的意義。但要了解此一問題之關鍵所在,則要先從一個較大的背景去理解。
二﹑兩大背景:儒家
首先我們要先回答以下的一個問題:當代新儒家究竟新在哪裏?
毫無疑問,新儒家「新」在以西方哲學來詮譯中國的哲學思想。例如,牟宗三先生以康德來詮釋儒家,唐君毅先生則用黑格爾,而勞思光先生則指出「開出說」是模仿黑格爾模型的想法[10]等,這些區分幾乎變了當代中國哲學的常識。
但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新儒家認為儒學具有高度的「宗教性」(religiousness),而此宗教性亦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即,儒家乃一道德宗教[11]。牟宗三先生對於儒家的宗教性說得最明白:
「此(儒家的)『內聖之學』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標是聖﹑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實意義則在于個人有限之生命中取得一無限而圓滿之意義。此則即道德即宗教,而為人類建立一『道德的宗教』也。……在儒家,道德不是停在有限的範圍……道德即通無限。道德行為有限,而道德行為所依據之實体以成其為道德行為者則無限。人而隨時隨處体現此實体以成其道德行為之『純亦不已』,則其個人生命雖有限,其道德行為亦有限,然而有限即無限,此即其宗教境界。」[12]
由此觀之,新儒家所理解的宗教實與我們一般日常所理解----多神或一神----有所不同。簡言之,宗教是人作為有限的存在不安於現實經驗世界而探求一無限--超越(the Transcendent)以求安頓現實生命。亦即是說,類似狄立克(Paul Tillich)認為宗教之普遍意義是:「信仰是在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時的心靈狀態。」[13]
但是,明顯的,儒家並沒有西方宗教,甚至是佛教,那種有系統的組織,例如教會﹑廟宇等,那麼儒家的宗教性如何在現世之中表現呢?
其實,答案就在於儒家對人及社會的看法之上。因為儒家認為,道德人格的實踐不可能在個体的孤立生命中完成,借海德格(Heigdgger)的用語,人是「與人的存在」(being with)[14]。而且,個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必具「參與」,這亦是建構理想社會的必要條件。所以,理想社會本身就具有終極性[15]。所以,儒家思想呈現的整個面貌,實非只是一道德的宗教,而是自我實現的道路與建構社會的原理之整合体[16]。
而此一理論的要求,則表現在「內聖外王」[17]此一理論的格局之上。而同時具有宗教意涵的外王,當然就出現了「教化」這一個概念。例如,孔子先富後教的思想。
《論語》,子路,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
所以儒家的政治理論中的教化觀念,同是亦為儒家理論的核心部分之一,不可廢。
三﹑對多元主義的理解
論說民主性質時,有很多人都以自由﹑平等﹑自決等概念作為立足點[18]。但是,有一個概念,或者說是事實,亦很重要,這就是多元主義式的社會。
本節所以用「多元主義的理解」作為題正是表達這種思想。而用「理解」而不用「定義」,是因為此一概念有很多歧義,例如:價值的多元主義,宗教的多元主義等,五花八門,而又語意不清。而且,如果要為多元主義作一定義,勢必落入價值的相對主義的複雜的討論及困境之中[19],所以我們只對多元主義作一相關的理解。
但此一相關之理解亦不是任意的,我們這個理解是對應著我們的問題:建構社會的原則。所以我們姑且叫這一種多元主義為社會的多元主義。我們如何理解這種多元主義呢?或者說,我們對於社會的多元主義究竟容納到什麼程度呢?明顯的,所謂社會的多元主義只能建立在政府的中立論旨上,即,政府面對什麼是理想的人生是採取中立的態度。因為,其實我們沒法接受或甚至實踐最徹底的多元主義----最極端的價值相對主義-----原因是,如果所有價值都是因人而異,都是相對的,則所有價值判斷都因此而不能成立,而亦不能構成一個社會。所以,我們在建構社會原則時,我們只能接受政府的中立論旨,亦即是,從積極面看,就是尊重原則;從消極面看,就是不產生支配的情況(domination)。
四﹑問題之構作
了解完以上兩個理論的背景後,我們可以回到先前的問題之上,就是開出說的理論意義。如果我們都接受以上對儒家及對多元主義的理解後,我們或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儒家「教化」這個概念會否做成政府對人民的一種支配呢?從而儒家是否與民主相矛盾呢?而此一問題的肯定項,亦變得有理論的意義與價值。
本篇論文的主旨就在於對「儒家『教化』這個概念會否做成政府對人民的一種支配?」這一問題進行考察。而「教化」此一概念實表現於「內聖外王」的理論格局之中,則「內聖外王」的關係對於回應我們的問題變得必要。
II. 本論
一﹑在傳統儒家內聖與外王的關係及其與多元主義的衝突
《大學》: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矣。」
由此可以初步看出「內聖外王」觀念中「王」與「聖」之間的關係。而此種關係明顯的是「跡本」的關係。聖與所以聖是「本」,理想的社會是「跡」。此中有著「由本顯跡」的關聯[20]。
值得注意的是,此中所言的「內聖」與「外王」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形式的表達。只能表現出道德修養與理想社會的建構有著邏輯上的關連,但沒有在內容上作出說明其之合理性。進而意謂著儒家的宗教性在介入外在世界的路徑時發揮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21]。因此,本節所要做的,就是對這種關係的合理性作出考察。
在本篇論的副題中,以「再檢討」而命名,其意謂著對於「內聖外王」的關係實已有不少的討論[22]。而本篇論本則借陳弱水先生在〈「內聖外王」觀念的原始糾結與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疑難〉[23]一文的分析作為基料,再次檢討「內聖」與「外王」之間的關係。
《論語》,述而,廿九。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論語》,雍也,二八。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憲問,四五。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上引文顯示出孔子對「仁」與「聖」有三種不同的層次。第一是「修己以敬」。第二是「修己以安人」,此即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境界,亦即「恕」道。第三是「修己以安百姓」或是「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是連堯舜都不易致的成就。而此中第一﹑二層,在孔子的理論中並沒有真實意涵的區分,因為「仁」這個觀念已就本身涵蘊著「度人」的奉獻[24]。所以這都可以歸於「仁」的領域。而「修己以安百姓」,則是「聖」的領域。所以兩者的不同點在於「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之上[25]。
而陳弱水先生認為,「仁」與「聖」分別由於和成德的問題不相涉,所以其分別只是一「量」的問題,而不是「質」的問題;是「成就」的問題,而非「修養」的問題—因為此中兩者都是成德的最高境界[26]。
但是這真的是「量」的問題嗎?這個問題我們容後再討論。
而「安百姓」的最重的中心課題就是「先富而後教」[27],在導論時已經引論,不敷。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安人」只是個人的修養問題,而「安百姓」則是一種社會行動[28],故此,儒家認為這種社會行動有賴於政治領袖的個人行為去實現。
總而言之,陳弱水先生認為,孔孟的「內聖外王」式的政治﹑社會思想的主旨在於:人的生命有內在的「善」,內在之善擴充至極的境界是人格發展的最高目標,實現此一目標的人格謂之「仁」或「聖」。理想的社會乃是合乎倫理原則的人際關係秩序(以生活豐足為前提),此一理想之完成端有賴政治領導者個人的資質,他具有影響整個政治﹑社會系統的動態。因此,「仁」或「聖」,執政是真正有效的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途徑,治國平天下的關鍵在個人的道德修養[29]。
而這一種理解,陳弱水先生作出兩方面的批評。第一,實際運用之困難。第二理論上之困難。就實際運用之困難而言,不外乎聖人如何有位的問題[30],因為本篇論文的論旨不在此,則這個問題就此打著。
至於理論上之困難,陳弱水先生則由他的理解分析「內聖外王」得出三個預設,考察這三個預設從而檢討「內聖外王」的合理性。我們就用「內聖外王」的第三個預設,以討論傳統儒家與多元主義的衝突。
第三個預設為:政治系統及其領導者應該也可以具有自足的道德資質[31]。
這個預設是否合理呢?我們先由討論政治﹑社會的「道德質素」的問題。美國當代神學家,政治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中指出:「……個人的道德行為和社會行為必須嚴格地與社會團體分開,不論是國家﹑種族或經濟團体……個人也許是道德的,他能為別人犧牲自己的利益。……但所有個人的這些成就對人類社會和社會團体而言若非不可能,便是極其困難。每一個人類團体都缺乏牽制衝動的理性﹑超越自我的能力以及對他人困境之同情。因此,團体的自利性實較表現於個人人際關係中自利行為更缺乏抑制。」[32]此中意思,實指政治在基本上是不道德及非理性的,因為「自利」是一切團體﹑階級或國家行為最高指導原則[33]。所以,社會的衝突—團体與團体之間的---必然存在。故此,在政治領域裏是不能希望有合乎道德原理的「理性的公正」(rational justice),而只能出現權力平行的「政治的公正」(political justice)[34]。
而這種現實主義者的看法,雖然陳弱水先生未能完全認同[35],但亦接受了此分析為一事實,所以也可以導致以下的論斷:縱然政治系統及其領導者可能會有偶然的自發道德行動,他們基本上絕不具有自足之道德資質。簡言之,陳弱水先生批評「內聖外王」的理論格局是範疇的誤用。
對於陳弱水先生的批評,我們為儒家作出辯護:儒家所討論的是應然之問題,而非實然之問題。縱然我們接受尼布爾的分析為一「事實」,但仍推論不出政治系統或領袖不應涵蘊道德的操手,因為尼布爾的分析不能推論出政治系統或領袖「必然」地不道德。
可是,這種回應是不能解決得了我們的問題。第一,如果我們以比較弱的立場去理解尼布爾的分析的話,則縱使我們認為生存原則與道德原則同等地重要的話,但是團体之間的利益衝突仍然會存在。第二,如果我們用第一點去理解尼布爾的分析的話,則這就正是我們要討論的多元主義的景況。所以,我們仍然能借用陳弱水先生對於這方面分析所得的結論,就是傳統儒家(以孔孟為例的)並不能解決多元主義下團体之間的衝突,而在政治領域中顯得軟弱無力。
二﹑新外王與多元社會模型
i. 新外王
對於陳弱水先生這類批評,當代新儒家作出了熱烈的回應[36]。但是,在我們替儒家作出一個可能的回答之前,我們又先看看當代新儒家如何詮釋「內聖外王」,從而轉化出「新外王」的思想。
當代新儒家在〈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下稱為〈宣言〉)中:
在過去中國之君主制度下,君主固可以德治天下,而人民亦可沐浴於其德化之下,使天下清平。然人民如只沐浴於君主德化之下,則人民仍只是被動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体仍未能樹立,而只可說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体。然而如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体,而不能使人民樹立其道德的主体,則此君主縱為聖君,而其一人之獨聖,此即「聖」為我有,即非真能成其為聖,亦非真能樹立其道德主体。所以人君若真能樹立其道德的主体,則彼縱以德化萬民,亦將以此德化萬民之事本身,公諸天下,成為萬民之互相德化。同時亦必將其所居之政治上之位,先公諸天下,為所可居之公位。然而肯定政治上之位,皆為人人所可居之公位,同時即肯定人人有平等之政治權利,肯定人人皆平等的為一政治主体。既肯定人人平等的為一政治主体,則依人人之公意而制定憲法,以作為共同行使政治權利之運行軌道,即使政治成為民主憲政之政治,乃自然之事。由是而我們可說,從中國歷史文化之重道德主体之樹立,即必當發展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乃能使人真樹立其道德的主体。[37]
根據當代新儒家這種詮釋,政治主体是道德主体求實現的過程中辯證地展現出來。這種解釋不但保存了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的理論格局,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君主制度「聖君賢相」的傳統政治格局之不足與「內聖」之矛盾,從而要求「內聖」與「外王」之間多一層轉折,以確立人在社會作為政治主体。更重要的是使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與政治之間只作為一種間接的關聯。使得道德及政治都有其各自的領域。而這就作為批評儒家的政治理論是範疇的誤用的最有力的回應。
ii. 「內聖」與「新外王」之間的關係
接住我們就應該問:心性之學與政治之間的間接的關聯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著實不容易地去回答,正如當代新儒家的民主理論經常受到一項批評:它僅停留在形上學的抽象層面,而不能落實到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具体層面上[38]。這類批評縱使基於誤解,但是並非全無道理可言,而事實上,當代新儒家對於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都是停留於形上學的原則的轉換上[39],所以我們借用康德的政治理論來作說明[40]。
當我們借康德的政治理論來作說明時,亦即是在問:在康德的政治理論中,道德原則與政治原則的關係是什麼?
康德的政治哲學之核心概念是「法權」(Recht),因為依其看法,共和憲政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為它是「唯一完全適合於人的法權的憲法。」[41]而「法權」此一概念之衍生,乃是由康德的實踐哲學的中心概念「定言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而來。定言令式為:「僅依據你能同時意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而行動。」即是,要求行為的格律之可以普遍化。而「法權就是使一個人的意念得以與他人的意念根據一項普遍的自由法則統合起來的條件之總合。」更精確地說,「法權」就是「定言令式」之外在化。所以,它們之關係就在於同是出自純粹實踐理性之要求,而其自身亦是一項形式原則,但是「法權」只規範人的外在行為,而不論其存心,而「定言令式」則否。
我們可以由這兩個概念的對照,引入另一對概念:「建構性原則」(constructive principle) 與「規範性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這對概念之引入,是因為在建構社會的過程中,「定言令式」扮演著「建構性原則」的角色,亦即是社會之所以建構之要求及指導規範原則的方向。而「法權」則為「規範性原則」,亦即如何地落實「建構性原則」之要求。由於「規範性原則」是處理「如何」的問題,則必然地會以現實的情況和環境而構成。而且,由於「建構性原則」----「定言令式」只有形式意義而無特殊之內容,則此原則對「規範性原則」亦只有形式意義,因此,「規範性原則」實亦有其獨立處理問題之領域。
由「定言令式」與「法權」之對照及「建構性原則」與「規範性原則」在建構社會之關係,則我們可以對於新儒家「內聖」與「新外王」之關係有一比較明白之了解。即「內聖」在建構社會的過程中是扮演著「建構性原則」的角色,因為新儒家所言的「道德主体之自我要求」[42],實亦是一種建構社會的要求,而這一要求實有一種理想性[43]。而此一理想性即構成一指導原則的特性。當然,對於「新外王」與「內聖」之關係,並不如「法權」這個概念直接由「定言令式」外在化而來,但是作為「規範原則」的「新外王」,實亦可由「道德主体自我要求」的普遍性而得到指導。此一普遍性,則表現在建構社會的理由之上,即是,人們之建構社會在於獲得幸福此一普遍性之要求之上[44]。
至此,我們已論說了新儒家對於傳統的「內聖外王」之改造,但這種討論,仍只是原則性地論說,則這種「內聖外王」的格局如何回應「儒家『教化』這個概念會否做成政府對人民的一種支配?」這一問題呢?
iii. 理論的改造:「命」的觀念的引入
明顯的,對於「內聖」與「外王」作為「建構性原則」與「規範性原則」,它們之間所謂「指導」的關係並不能真正規限政府對社會的行動,其原因在於「指導」一詞的含混性。
要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種解法方法就是引入「命」這觀念到「內聖外王」的架構之中。為了說明這種理論改造的必要性及合法性,則我們借用勞思光先生在〈理性與民主〉[45]一文中對於「單一主体的境域」與「眾多主体的境域」之差異作一說明。
「……道德心即在一一事上實現之自覺心,此心為一主体。……心靈如此活動,可以宋儒所說『一心應萬事』之義描繪之。一心萬事,在在如理,次為道德心之直接運行。在此運行下,對於每一道德心說,其他一切人一切事皆成為對象;因其他的心靈之活動對此心言,亦成為一一事件;……這種自覺心的活動,乃由各方面建立互相隔斷之單一主体;說隔斷因為每一主体皆將其他主体化為對象而攝受之;故主体與主体間實無交通,一有交通則各變為對方所攝受之對象;於此,眾多的主体乃為各有一天地者。」[46]
此乃就單一主体之境域作一描述,勞思光先生認為,對於攝受形式之主体溝通在道德及宗教領域之中實無問題[47],但在公共事務上或政治生活中,則見一問題。
「……此問題即是通往權力問題。
『一心應萬事』,此萬事均隸屬於此一心下,但倘有一事,不屬於一人,而為眾人所共,則眾人眾心中那一個能為萬事之主?此問題與一一事非問題迴異,而是一權力問題。」[48]
所以,此一實因是眾多主体並立之境域。
「若是眾心中隨取一心為主,則其他心靈即受到不正當之抑壓,換言之,眾人所共之公共事務,如由任一人決定,則此其餘諸人皆失去作主之地位;而成為被處理之事象或材料;在這種情形下,其餘眾人對於有關自己的事不能自己決定,其意願及知識皆不能表現,即為一不正當之情況。」[49]
而且,勞思光先生引用黑格爾對國家的看法,對於以上那種不正當之情況批評為專制政治,而專制政治因為人不能在其中高度發揮其自覺能力,故亦不能算是一真正的國家[50]。
故此,其解決的辦法是:
「就公共事務說,此問題乃在眾多主体並立之境域中成立者。唯有將一一人皆當作主体看,纔有此問題,而人之當作主体,其關鍵全在理性之肯定,因離開理性,則人之主体性即不能顯出。」[51]
其實這裏所言之理性,就是實踐理性,即是對於價值問題的自覺心,亦可以為道德心[52]。
觀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在政治領域之中眾多主体並立之重要性。「內聖」要而轉出「外王」,正視眾多主体並立境域此變得必要。而要完成此一任務,則「命」這一觀念起了極大之作用。
在看此作用之前,先對其引入之合法性作一簡述。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牟宗三先生在《圓善論》中認為,孟子不直接名「仁義禮知聖」為「性」,因為雖然是「性」,但亦有「命」的成分。而「命」這概念,勞思光先生說得很清楚:
「說『性也,有命在焉』時,此『性』字自是『本有之功能』之義;而『命』字則取『限定義』。……合言之,即謂:凡屬被決定之功能,皆不表主体性。……而『命』字在意義上則為『命定』之意,所指涉者則包括經驗界之一切條件系列。」[53]
所以,君臣之關係,即現代社會之政治結構,在傳統儒家之思想系統之中,亦可以認同其中有「命」之領域。
而就〈宣言〉所言君主應該開放其君位於天下,此時人民即面對其眾多主体並立之境域,因為所有人都以政治之主体而存在著,而此一境域之中的所有問題之解決原則,則實屬「命」的領域。而此一「命」的領域,亦同於勞思光先生所言,所指涉者則包括經驗界之一切條件系列。所以,所謂「內聖」作為「建構原則」指導「外王」作為「規範原則」時,其「指導」只意謂以用何種政治的方式去實行「內聖」以達至「眾多主体並立」之境域要求----人能在其中高度發揮其自覺能力。而亦因此,「內聖」之指導只能是對於民主政治制度之形式要求,並對政治之內部之原則運作及對社會的具体政策並無合理﹑合法之影響力。
III. 結論:教化在多元社會之模型下之作用
至此,我們已論說了儒家「內聖外王」的理論格局作為多元社會之模型之可能性。而亦可對「儒家『教化』這個概念會否做成政府對人民的一種支配?」這一問題作一較圓滿之解答。
蓋因儒家的道德理論(「內聖」)只能作為建構社會的「建構原則」,而「規範原則」即在於民主制治之制度之上,而政府之成立,即在於使其制度之運行得而充分地表現於社會之上,則在於政府之義務而言,其最首要之要務是維持社會之和諧與提供一個給所有人作為自由表達自己的場所,故道德理論亦不能對社會內部運作及對社會的具体政策作合理之影響力,亦即是說,政府面對什麼是理想的人生是採取中立的態度。所以,「教化」之觀念,在政府的立場而言,只有消極意義,是一界限的概念。
這個界限之概念,我們可以作進一步之說明。因為建構社會之理由在於所有主体之要求於建立理想之生活之上,則就其必要條件而言,即是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生活都能比作為不建構社會之前的生活要好,社會才能因此而建立。所以政府並不是完全沒有限制地給與在社會中每一個人自由。其限制即等同於「教化」之觀念。而明顯的,不傷害他人及自己的原則是政府接受市民生活方式的最後底線,不過過此以住,政府就不能合理地對市民作出任何道德上之干預。故此,政府亦非真的是對什麼是理想的人生是採取中立的態度,而只能是對什麼是最理想的人生是採取中立的態度。
---------------------------------
[1]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和唐君毅合著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第九節〈中國文化發展與民主建國〉,文收唐君毅:《中國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台北: 學生書局,1975),下冊附錄四,頁865~929。
[1]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和唐君毅合著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第九節〈中國文化發展與民主建國〉,文收唐君毅:《中國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台北: 學生書局,1975),下冊附錄四,頁865~929。
[2] 同註1。
[3] 同註1。
[4] 同註1。
[5] 關於這埸論戰的始未及所涉及的問題,請參看李明輝: 〈徐復觀與殷海光〉,文收李明輝: 《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6] 例如,勞思光先生在《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的第八講〈認識與路向〉中即不指名道姓的批評「開出說」在實踐上的必要性。勞思光: 《中國文化路向文題的新檢討》,(台北: 東大圖書,民國82年)。
[7] 「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乃是唐君毅先生的用語。參看唐君毅: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 三民書局,1974)。
[8] 有關於五四時期的反傳統主義請參看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rth Era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consin Press, 1979); 中譯為: 穆善培譯: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淚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 人民出版社,1988)。或是參看勞思光: 《中國文化路向文題的新檢討》,(台北: 東大圖書,民國82年),第四講〈中國文化運動與五四思潮〉,頁73~85。
[9] 這種文化有機或整体論的思想,大体可由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未死的理由之一--當下即是—引申出來。而且,從新儒家反對只對民主制度的學習而完全推翻中國傳統文化是行不通是因為這時的民主是「無根」,可以看出。同註一,第三節〈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及第十節〈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
[10]同註六,頁123~126
[11] 有關儒家的宗教意涵,請參看牟宗三: 《心体與性体》,(台北: 正中書局,1968) 及唐君毅: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 正中書局,1953)。另劉述先: 〈儒家宗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文收於氏:《生命情調的抉擇》,(台北: 志文出版社,1974),頁43~63。
[12] 牟宗三: 《心体與性体》,(台北: 正中書局,1968),頁6。
[13]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 (Harper &Row, 1958), P.1.
[14] 此中的意涵,可以參看杜維明著,曹幼華﹑單丁譯: 《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江蘇省新華書店, 1991)
[15] 參看陳弱水: 〈「內聖外王」觀念的原始糾結與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疑難〉,文收於《史學評論》,第三期,1981,頁79~116。
[16] 同註15,頁83。
[17] 「內聖外王」本不是儒家的用語,而出自莊子天下篇。但此一觀念借到論說儒家的基本政治理論的格局,而源遠流長,而且實亦不有任何不當之處,皆因此概念只有形式意義。
[18] 例如,柏林(Berlin),洛爾斯(J. Rawl),德我肯(R. Dworkin)等,參看石元康: 《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台北: 聯經,民84年)。
[19] 有關價值的相對主義所構成的多神主義(polytheism)的困境,請參看石元康:〈多神主義的困境-----現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問題〉或〈傳統,理性,與相對主義-----兼論我們當前該如何從事中國哲學〉,前者文收氏著: 《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台北: 聯經,民84年),頁177~194;後者則文收:《當代新儒學論文集—外王篇》,(台北: 文津出版社,民80年),頁261~286。
[20] 同註15,頁84。
[21] 同註15,頁85。
[22] 例如,除復觀:〈儒家在修身與治人上之區別及其意義〉,文收氏著:《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北: 學生書局,1988),頁203~220。
[23] 同註15。
[24] 同註14。
[25] 此是就仁與聖的不同而言,而在論語之中,此兩者有時亦實無二至。
[26] 同註15,頁90。
[27] 《論語》,子路,九。
[28] 同註15,頁92。
[29] 同註15,頁101。
[30] 同註15,頁93~101。
[31] 同註15,頁108。
[32]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53), pp xi~xii.
[33] 同註15,頁109。
[34] 同註32,頁31~32。
[35] 同註15,頁111。
[36] 這裏所指範疇的誤用其實亦即是對儒家作為「泛道德主義」的批評。對於新儒家的回應,可參看李明輝: 〈論所謂「儒家的泛道德主義」〉,文收於《當代新儒學論文集.總論篇》或陳特: 〈唐君毅先生的文化哲學與泛道德主義〉,此文亦文收於《當代新儒學論文集.總論篇》(臺北 : 文津出版社, 民國80年)。
[37] 同註1。
[38] 關於這方面的批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勞思光先生對於模枋與創新之間的區別與對中國文化當前情勢的分析,參看勞思光: 《中國文化路向文題的新檢討》。另外,陳忠信先生的〈新儒家「民主開出論」的檢討〉及楊儒賓先生的〈人性﹑歷史與社會實踐—從有限的人性看牟宗三的社會哲學〉,皆文收於《台灣社會研究》,第1卷,第4期(1988年冬季號)。
[39] 就以牟宗三先生為例。牟宗三先生用「分解的盡理精神」與「綜合的盡理精神」的區分來分析西方與中國歷史發展的不同精神型態,說明西方的民主與儒家的理論特徵。再以「理性的運用表現」及「理性的架構表現」這對概念如何以「良知之自我坎陷」由前者轉化到後者,此一儒學內部的辯證過程,從而由「內聖」「曲通」「外王」。但此一說法仍只在形上學的原則轉換之上,其中只表明原則上可行,故只有邏輯的規限義意,而沒有內容義意。此中概念之詳細關係,請參看牟宗三: 《歷史哲學》,(台北: 學生書局,1984)頁181~183。及氏著: 《政道與治道》,(台北: 學生書局,1987)。另何信全: 〈儒學與現代民主的融通—牟宗三政治哲學探析〉,文收於劉述先主編: 《當代儒學論集: 挑戰與回應》,(台北: 中研院文哲所,民84),頁131~158。
[40] 這裏所用的康德的政治理論是參照了李明輝先生的論述。參看李明輝: 〈性善說與民主政治〉,文收於劉述先主編: 《當代儒學論集: 挑戰與回應》,(台北: 中研院文哲所,民84),頁183~188。
[41] 共和憲政: 即是採用共和制憲法的政治形式。依李明輝先生的說法,康德所用「民主」一詞乃按照古典意義來使用,而與「獨裁主義」(Despotism)相對的「共和主義」(Republikanism)則反倒相當於今日意義的「民主」。
[42] 同註1。
[43] 參考牟宗三: 《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 私立東海大學,民84年)。
[44]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不是說康德的定然命令與法權就是內聖與外王,這裏借康德的政治理論的理由在於說明建構原則與規範原則時之間的關係作為一個例子。
[45] 勞思光: 〈理性與民主〉,文收氏著: 《文化問題論集》,(香港 : 自由出版社, 民國46)。
[46] 同註45,頁217。
[47] 因為在道德領域是處理應然之問題,宗教領則涉及超越化之運行,同註45,頁217,226。
[48] 同註45,頁217。
[49] 同註45,頁218。
[50] 同註45,頁218。
[51] 同註45,頁218。
[52] 同註45,頁225。
[53] 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 三民書局,民84),頁197~198。
參考書目︰
1.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和唐君毅合著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第九節〈中國文化發展與民主建國〉,文收唐君毅:《中國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台北: 學生書局,1975),下冊附錄四,頁865~929。
2.李明輝: 〈徐復觀與殷海光〉,文收李明輝: 《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3.勞思光: 《中國文化路向文題的新檢討》,(台北: 東大圖書,民國82年)。
4.唐君毅: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 三民書局,1974)。
5.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rth Era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consin Press, 1979); 中譯為: 穆善培譯: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淚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 人民出版社,1988) 。
6.牟宗三: 《心体與性体》,(台北: 正中書局,1968) 。
7.唐君毅: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 正中書局,1953)。
8.劉述先: 〈儒家宗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文收於氏:《生命情調的抉擇》,(台北: 志文出版社,1974),頁43~63。
9.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 (Harper &Row, 1958) 。
10.杜維明著,曹幼華﹑單丁譯: 《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江蘇省新華書店, 1991) 。
11.陳弱水: 〈「內聖外王」觀念的原始糾結與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疑難〉,文收於《史學評論》,第三期,1981,頁79~11。
12.石元康: 《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台北: 聯經,民84年) 。
13.石元康:〈多神主義的困境-----現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問題〉,文收氏著: 《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台北: 聯經,民84年),頁177~194。
14.石元康:〈傳統,理性,與相對主義-----兼論我們當前該如何從事中國哲學〉,文收:《當代新儒學論文集—外王篇》,(台北: 文津出版社,民80年),頁261~286。
15除復觀:〈儒家在修身與治人上之區別及其意義〉,文收氏著:《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北: 學生書局,1988),頁203~220。
16.孔子:《論語》。
17.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53) 。
18.李明輝: 〈論所謂「儒家的泛道德主義」〉,文收於《當代新儒學論文集.總論篇》(臺北 : 文津出版社, 民國80年) 。
19.陳特: 〈唐君毅先生的文化哲學與泛道德主義〉,此文亦文收於《當代新儒學論文集.總論篇》(臺北 : 文津出版社, 民國80年)。
20.陳忠信先生的〈新儒家「民主開出論」的檢討〉文收於《台灣社會研究》,第1卷,第4期(1988年冬季號)。
21.楊儒賓先生的〈人性﹑歷史與社會實踐—從有限的人性看牟宗三的社會哲學〉,皆文收於《台灣社會研究》,第1卷,第4期(1988年冬季號)。
22.牟宗三: 《歷史哲學》,(台北: 學生書局,1984)頁181~183。
23.牟宗三著: 《政道與治道》,(台北: 學生書局,1987)。
24.何信全: 〈儒學與現代民主的融通—牟宗三政治哲學探析〉,文收於劉述先主編: 《當代儒學論集: 挑戰與回應》,(台北: 中研院文哲所,民84),頁131~158。
25.李明輝: 〈性善說與民主政治〉,文收於劉述先主編: 《當代儒學論集: 挑戰與回應》,(台北: 中研院文哲所,民84),頁183~188。
23.牟宗三: 《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 私立東海大學,民84年) 。
27.勞思光: 〈理性與民主〉,文收氏著: 《文化問題論集》,(香港 : 自由出版社, 民國46)。
28.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 三民書局,民84) 。
29.孟子:《孟子》。
1999/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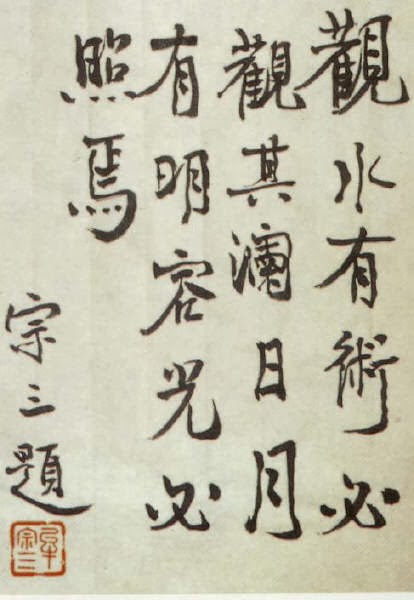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